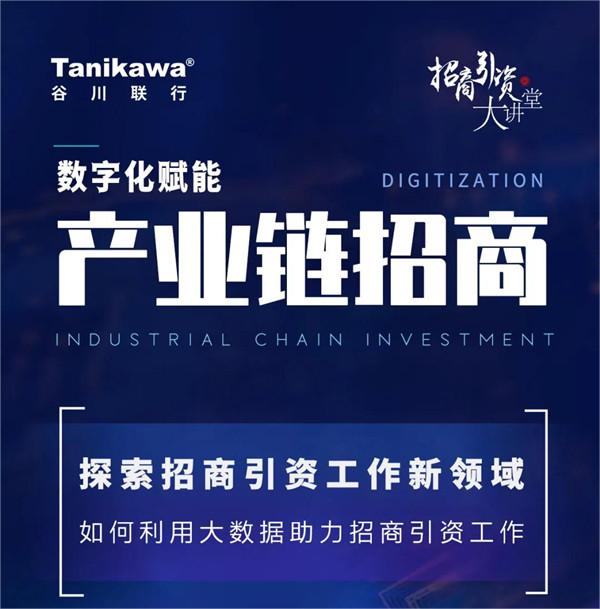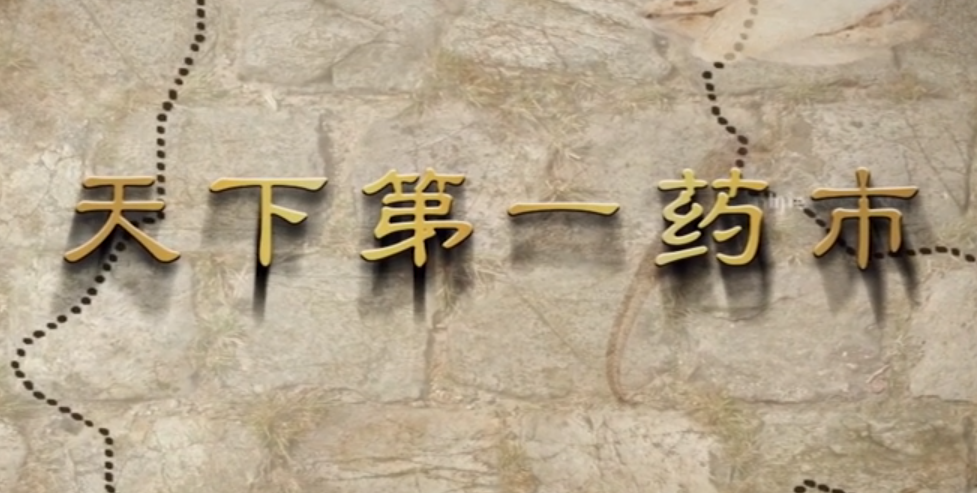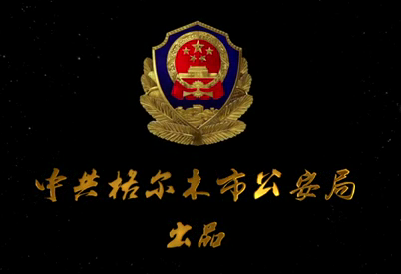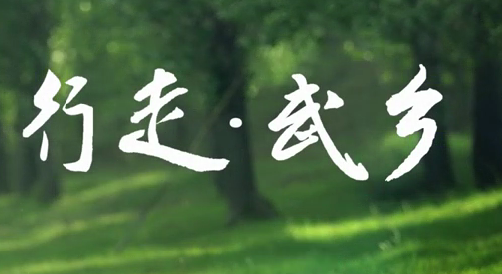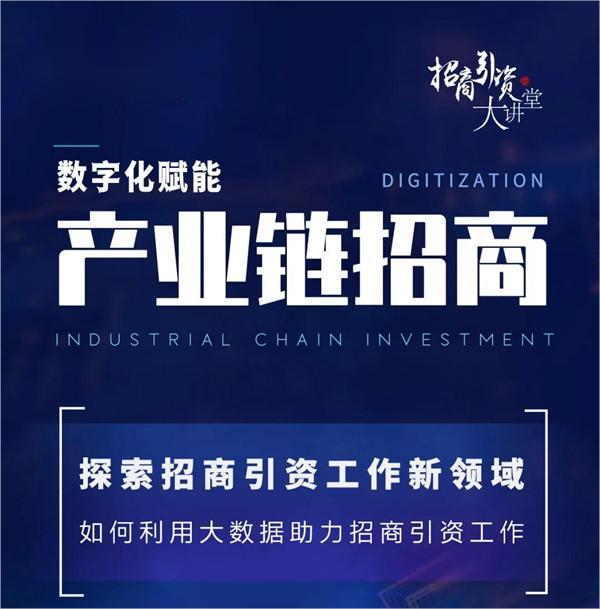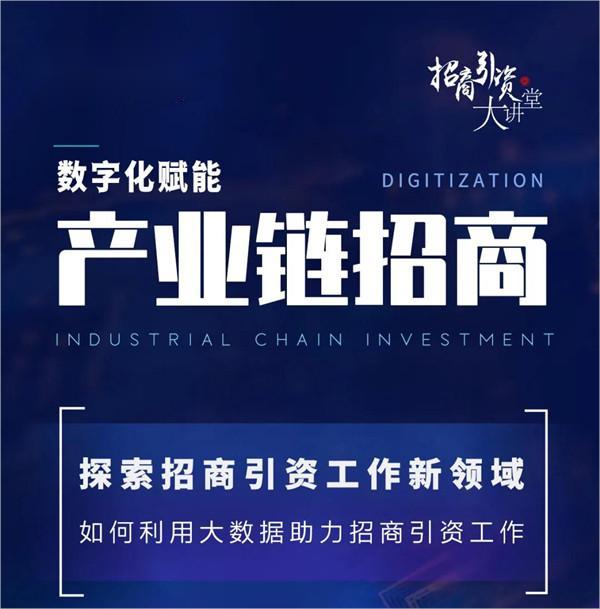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演变,多边治理机制面临更大压力;贸易保护日益加剧,一些国家组织建立“芯片联盟”,愈发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缩影响持续累加,世界经济“滞胀”特征明显;金融脆弱性凸显,从美国中小银行接连关闭,到瑞士老牌银行瑞士信贷银行被迫出售,再到德意志银行股价暴跌,国际银行业稳定性迎来重大挑战……受多重不确定因素影响,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
在4月4日召开的2023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年会上,多位嘉宾在发言中如是总结当前经济金融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加强政策协调配合,稳定市场预期,成为金融监管面临的重要课题。
外部压力下探索应变之路
法兴银行亚太区研究部主管、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姚炜从外部和内部、周期和非周期因素出发进行了分析。“外部冲击下必须进行政策调整。比如,疫情就是外部非周期因素,这种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怎么进行政策工具的选择值得讨论。”她表示。
过去几年里,中国也在用行动和实践回应这个问题。中国进出口银行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杜希江介绍了该行如何发挥政策性金融的逆周期跨周期调节作用。杜希江表示,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进出口银行积极行动,出台了支持稳住经济大盘、支持上海抗疫复产、加大基础设施信贷投放、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等专项措施,以空前力度投放外贸信贷,并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置于突出位置。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当前新“三驾马车”的投资重心要尽快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制造业方面,要支持体现技术进步的设备投资,同时要加大对数字技术和绿色创新的投资。从出口角度看,刘世锦分析表示:“稳定制造业比重,意味着在全球竞争中具有相对优势,客观上要求稳定出口比重。”
这也正是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据杜希江介绍,进出口银行瞄准制造业发展制高点,助力振华重工高端港机装备出口至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00座码头;支持中老铁路、蒙内铁路建成通车,有效带动中国铁路设备、技术、标准“走出去”。此外,围绕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两个重点,进出口银行不断创新产品,实施与国际标准接轨的绿色信贷政策。
对于疫情防控期间的一些政策工具效果,姚炜进一步表示,世界范围内,当前通货膨胀现象非常严重,一些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疫情暴发时或许不应该使用量化宽松工具,开一些流动性的窗口可能就足够了。“当下次外部非周期性因素发生时,这种反思为我们选择应急性工具还是周期性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她表示。
从当前情况来看,姚炜认为,需要关注的外部因素是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的影响。她表示,我国或其他新兴市场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准备和政策选择,来减小由外部加息环境带来的影响。“这方面政策选择主要包括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变化。我们研究发现,美联储加息周期对我国汇率、利率还有股票市场的影响都相对较小,说明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起到了防范外部风险的作用。”姚炜认为。
应对内生变化 政策需有前瞻性
与外部因素相似,内部因素也存在周期和非周期因素。姚炜表示,对于一些内生因素,不能等到周期发生变化才进行协调,在周期中就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进行监管的调整。
“金融监管应在大潮没有退去之前把大家管起来,不要做裸泳者。”姚炜表示,“当前美国这种流动性过度集中,甚至集中在某个行业的情况。”她表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实践的政策框架,如控制影子银行等,为金融稳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观察当前的国内发展,杜希江表示,可关注如下几重变化:一是经济增长势头的变化。近几年,我国经济遭遇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经济下滑势头得以遏制。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二是内需复苏动能的变化。杜希江认为,在前期政策强力支持下,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快速增长,成为稳定内需、托底经济的主要抓手。随着疫情快速达峰过峰,此前恢复偏慢的短板领域迎来明显反弹。
这种变化下政策应该如何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刘世锦提出,发展实体经济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准。对于一些人提出的“金融、房地产、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的观点,刘世锦表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数字经济是全球近来的新潮流。“我们需要反对和抵制人为制造泡沫、自我循环、商业欺诈、行政性垄断、不正当竞争等,但不是简单地否定某些领域和部门。”他认为,要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基准,防止误解走偏,这样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
同时,刘世锦提出,要着力支持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解决农民工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以此作为扩大内需、扩大消费的重要途径。
加强协调配合 形成政策合力
本次年会上,多位嘉宾提出,在制定宏观政策时要寻求政策联动和合力。在姚炜看来,比较好的模式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在进行前瞻性微调的同时叠加金融监管配合。
对此,北京金融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文红进行了更系统的阐释。她认为,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监测和评估很难由一家机构独立完成。“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政策的协调配合还需要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的充分信息交流和共享。”她表示,二者均具有各自的专长和信息优势。比如,中央银行比较熟悉整个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监管机构则比较熟悉单体机构和相关行业的业务模式与风险状况。
李文红认为,为了提高宏观审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需要加强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之间的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通过深入分析、经验判断和交流讨论,研判金融机构在风险暴露方面的共性特征、相关性、经营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趋势、风险水平与特征,及时发现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如何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以稳定市场预期?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姝从地方省域层面谈到了浙江的一些具体实践。她表示,当前的经济政策要求更加注重协调发力,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社会政策,要加强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在具体实践中,据陈姝介绍,浙江省各部门同步研究部署,综合形成了“8+4”政策体系,即扩大有效投资、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等8个重点领域政策包以及财政金融、自然资源、能源和人力等4张要素保障清单。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她介绍,浙江省实施“千项万亿”扩大有效投资的计划,在金融要素政策上加强商业银行对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签约项目的配套融资支持,完善银项精准对接机制,深化“险资入浙”行动以及支持符合条件的存量项目通过REITs等工具盘活资产。
“这个政策体系包含了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各个领域,是一个需求侧和供给侧、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要素有机结合的整体。其中,金融要素政策更加凸显精准有效,要优化投放结构,更好发挥金融的血脉作用。”陈姝表示。